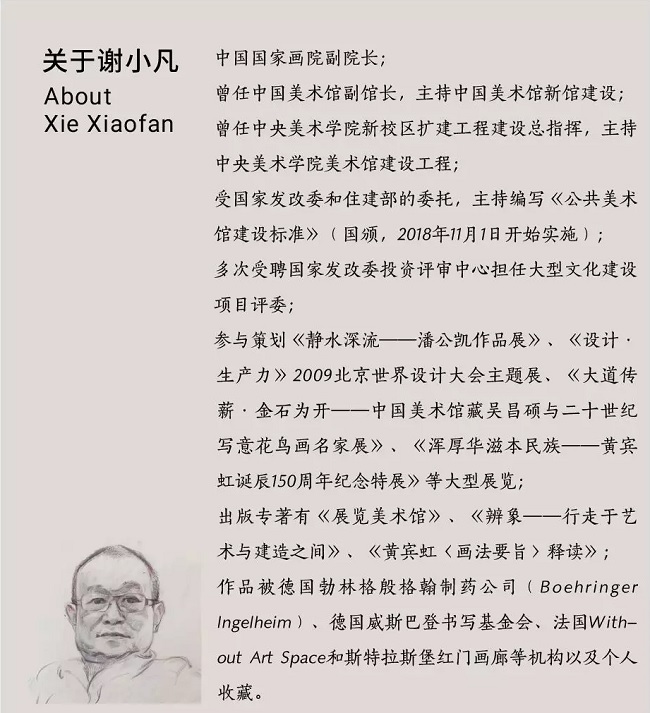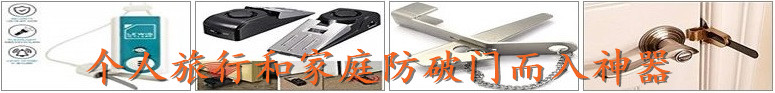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谢小凡印象
(《世界华文媒体》记者吕芳,《国际艺术新闻网》特约记者大奔、记者王萌2019年10月31日北京中国国家画院报道)初识谢小凡,印象最深刻的竟然是他对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建设的巨大贡献以及他对国家公共美术馆建设标准的订立。这一国颁标准自2018年开始全国实施。谢小凡说:“邂逅美术馆,承担建美术馆的基建任务是他做梦都没想到的事。以前从事的职业完全与这个行当无关。至于怎么做可行性研究报告则是从头学起,头脑中对这一段程序完全是一片空白,正是这段空白给了他勇气和力量”。
北京深秋的暖阳洒在画院大门古朴的雕梁画栋上,映得“中国国家画院”几个绿色大字愈发熠熠生辉。跨过门槛未几,迎面而来就是一条古色古香的九曲游廊,两边自是亭台轩榭,假山池沼。锦鲤戏水,香鸭逐波,秀木葱郁,修竹姗姗。好一个微型苏州园林!曲径通幽处,工作人员把我们引到了二楼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谢小凡的办公室。在他陈设简单的办公室里,我们一开始就直奔主题请他谈谈中国美术馆和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的建馆情况。谢小凡递给我们他写的《展览美术馆》,说所有的信息都在这本书里。




朱青生为他这本书所写的序里有两段话这样说道:如何建造一个美术馆,如何在中国建造一座“正确”的美术馆。只有建成美术馆的人,才能给出解答,恰逢他愿意,而且能够。的确,四顾难觅,此何人哉?;谢小凡受美院之托,仔细倾听,透析难题。以为借鍳,车辙虽然繁复,视察全赖眼光,中国待兴之时多借发达国家经验,取经而西行,顾盼入微,把他国美术馆的建设与其国情民风的关系细细参悟…….‘事非经过,不知难’,谢小凡先为其难,天下将得其便利,甘苦正在此书中,里外之间,正有云起……
谢小凡在《在矶崎新获普利兹克奖时》和《矶崎新接受颁奖时》里把建造中央美院新馆的日本建筑大师矶崎新称作是他美术馆知识的“早期的启蒙者”、“启蒙者”、“再启蒙者”。称他是所有建筑师中最具文人气、最具先锋精神,融合得至中至正的唯一一个,也不为过。他也大谈让•努维尔,中国国家美术馆的设计师,大赞他的“沙漠玫瑰”及阿布扎比的卢浮宫分馆。如果说凝固的音乐是建筑,那么他就反其道而行之,靠光线对建筑的反射,把建筑当做变化来做,消解了大的房子容易给人造成的恐惧感和压迫感。
美术馆不是一个外型。外型只是美术馆的建筑,或者表象。展览这一概念,是现代的,是公共的,通俗地说,把作品放置在展览馆内,供认识或不认识的人看,以达到审美、传播、教育等目的。美术馆又不能不首先是一个外型,一个标识,一个情性的凝结。喧嚣于众目之中而苏世独立,招摇在群殿之上而非比寻常。亲切迎合着芸芸众生,诱之以美丽,潜化在崇高。中央美院新美术馆从最初的一个聊出来的建新馆的想法,矶崎新一出手,就把创意与实现做了有效的控制。谢小凡感叹“大师与常人设计的区别在于创意之初便想到了实现的可能”。时年72岁的矶崎新是个纯粹的艺术家,只为名不为利,履行了他“将设计费全部用于建筑”的诺言。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验收合格,矶崎新将其在中国确立事业的丰碑,留在一个伟大民族最高学府的门旁。谢小凡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默默地在其中解决了成千上万的琐务细节,眼光所到之处也必定是他人难以企及的远方。
谢小凡迄今从来不厌倦的三件事:一是做饭,二是写日记,三是看书,尤其是哲学方面的书。在《展览美术馆》里,他说:“我有写日记的习惯,几年积了好多本。翻开日记,满篇是矛盾与妥协,天天都新鲜,即使像流水帐,但充满客观。好不容易把成千上万件啰嗦事归纳成两页,是为了让读者好看。有人建议就拿几本日记去出版,我则以为随意”。作为建馆的总指挥,上到与矶崎新、让•努维尔这样的国际级大师沟通,下到与“老实肯干的工人老大哥同甘苦,共患难”,事必亲躬不耻下问。凡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平和而淡然。他说不论在哪儿,要做成一件事儿,没有一个环境和团队的支持是不能成的,他珍惜大家对他的信任。所以再苦再累,每天总是高高兴兴地上班,心中灿烂。好不容易干成美术馆,苦也变成了甜。心中藏着一句就是“感谢上下左右对我的关怀和培养,真的”。
在跟矶崎新建馆的几年时间里。谢小凡把工作的点点滴滴,林林总总,细致完整系统性记录了下来。因为喜欢哲学研究哲学,故思想上能跟大师碰撞出许多思想的火花,能快速领悟、感悟、禅悟出大师的许多建筑理念以及施工技巧,不容易去做钻牛角尖。这样一路摸爬滚打,掌握了如他所说的“没有任何一所大学能教给我这么多本领”,这对于他日后为国家对美术馆建设标准的订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谢小凡办公室张贴着一些趣味盎然又俏皮的画,我们转而聊到了“正题”书画艺术。作为中国国家画院的副院长,前任个个都鼎鼎大名如李可染、黄胄等,问他有否思想压力。他竟脱口而出表示“完全没有”, 这倒使我们有些愕然。他解释说一则他刚调入国家画院,还在熟悉工作、与团队磨合中,二则中国国家画院主要是做美术研究的,理论性较强。他本人指挥过美术馆的建造,主持过美术馆建筑设计的国际招标,主持编写了《公共美术馆建设标准》(国颁),从事过美术馆藏品、民间艺术的管理工作,早年还在四川攀枝花市委宣传部工作过。所干的每一项工作都是他的老师,在实践中学习。领悟到的东西都切实,变成画与文字,竟有些道成肉身的意思。他在基层干过,那是生活的洪流,他极其珍视,那也是他的信仰。于是他的画变成了一个窗口,而这个窗口正是他自已。
一日,谢小凡看着从外地寄来的没吃完的过了期的月饼和攀枝花老家寄来的石榴,他脑海里一闪而过美国二十世纪初艺术家波洛克作画场景,于是,三下五除二把干瘪了的石榴捣成汁,和墨汁相伴,变成了一幅画作《中秋的汁》。后来出差公干,手上无礼品,便把作品一分为四分别装裱送人。受画者中有通过招标进来建造中国国家美术馆的法国设计师让•努维尔。画的名字和意义都是后来封的。
卡纸宣纸边角余料都舍不得扔,谢小凡便用来试墨。可能是受波洛克的影响太深,痕迹积累多了,成了图案时,他便会想到用水印木刻的方法把它做成版画,然后依其形状再取名字。看着朋友送他的木塔,他就会常常想起他去参观过的这个辽代建筑,脑海里总现出那木塔斑驳的样子,于是倏然间一幅“风雨剥蚀图”就诞生了。画名和字体的歪歪倒倒暗示了岁月的沧桑。看到朋友的乌木镇纸,他也会突发灵感,将没有刻字的那面反过来,迅速涂上墨汁,盖在画上,画风变成了一群挤在一起的可爱的牛。
因为建造中国美术馆,他跟让•努维尔有了更多的接触。法国人的浪漫气息似乎也感染了他。一句“男人活着的意义就是赞美女人”,让他画中的“色相”滚滚而来,不论是对着天空的呐喊,还是对“乌纱帽”的思考,抑或跟让•努维尔那一个月里工作上的争争吵吵,再有就是他再次提交的计划方案,谢小凡都把它们画在画布上,统统附上了丰富的色彩。
书画界的谢小凡还真的不好定义。他说画水墨画吧,真的没人教过他,只是零距离见过潘公凯做大画,算是唯一“身教”的老师,也算是无师自通吧。他认为传统意义的中国画,其存在方式是小范围的,就像他学过的“文人画”吧,他说那是苏东坡的创意。画卷拢在袖子里,邀上三五知己喝酒行令,酒酣之时,掏出画轴展而示众。于是众人争相效而仿之。说波洛克影响了他,好象有一点,他常用行动做画;说黄宾虹影响了他,也对,因为常揣摩他的积墨要旨而画出《我们这个年代的雾》。“很多艺术家在一起跑,很多人半路倒下,有的也跑出了轨道,真正能奔着单纯去的那位,最后就成了大师。”他在欧洲考察期间看了众多的博物馆,“突然觉得艺术这点事,完全与天赋相关,不是汗水与努力所能及,是上帝的安排。”他作画就像写日记一样,随性随意。他说写日记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近几年有写不过瘾的感觉。所以,有段时间,他在办公室支起架子画日记。天天没有目的地画几笔,积累出模模糊糊的形象,经月而成。
他办公室挂着一幅小猪图。他说每年都会习惯性画一套猪年、狗年之类的,这些都是早上起来喝茶时随性所做,至于日后别人赋予了它们以价值,这完全不是当初他所能预料,和他那一段也没有任何关系。他说如果想到作画是为了卖钱,或者是为了送人,他会有压力,他说现在做艺术展览,一进去就知道作品是不是带有目的性。中国画里很考验人的是去目的化。办展览是为了宣传,宣传是为了价格,价格是为了销售,销售是为了改善生活,这是顺理成章的,没有错。可是一想到这个东西,马上就会出问题,这样压力就来了。所幸他还有一份工作,生活没有压力。
当问及艺术家与生存的问题时,谢小凡说起有次他去洛阳,恰逢“洛阳牡丹节”的旧事:整条街道都在画牡丹。一幅大画只要150至200元,竞争激烈。画家该如何生存?他买了几张带回来思考。他边说边兴致勃勃地拿出来给我们看,问我们有何想法。牡丹图上花团锦簇,朵朵牡丹娇艳欲滴。不等我们作答,他便幽默地说出他的生存之道:他会考虑把这张大画分开变成几份,剪下牡丹花来进行再创作,把它变成他自已独特的东西,再让我们带到加拿大去卖,换取加币,让作品升值,又或者,就像街上画牡丹的画家一样,放下身段,勤奋工作,把艺术品当成一个为生活增光添彩的装饰品,降低价格,争取高产,以量取胜,把劳动就变成生产资料,因为画家要吃饭,要生存,就必须要让艺术与金钱挂钩。如果要把艺术当成纯粹的艺术产品,它就是一种精神产品。精神产品没有衡量尺度,谢小凡的度量方法就是看其独特性和唯一性,看其有没有特征,有没有思想,就像人们买衣服一样,看有没有创意。对于目前艺术家生存难的问题,他拿毕加索举例。大家看到的事实是中国近期十年来绘画市场的繁荣,但是纵观世界艺术史,绝大部分都不是活着的艺术家能反映的。

在大同的时代,“不同”是多么的重要。而谢小凡,就是那个“不同”。他不仅仅书画自成一家,搞建筑又更胜一筹,作为哲学爱好者,他的思想是深遂的。他跟矶崎新有共同的观点:人的身躯只是一个灵魂寄托的容器,灵魂是不灭的,所以他的作品一如矶崎新的作品,都有它的魂。作为一个普通人,他又是有烟火气息的。这就是我们通过采访认识到的一个不一样的谢小凡。谢小凡认为,艺术和艺术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可同日而语:艺术、艺术创作是一种精神层面的活动,是不用于交易的,也无法用价值来衡量艺术家的艺术思考;而艺术品显然是一种物质、一种装饰生活的产品 ,是产品,就可以交易,而这种交易行为构成消费者、市场价值与艺术品之间的物质关系,与艺术家和艺术家的艺术认知、探索没有直接关系。艺术无价,艺术品有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