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越:雷蒙·阿隆与萨特的世纪之争(一)
雷蒙·阿隆与萨特的世纪之争(一)
——基于一场“思想战争”的法国战后思想史
鲁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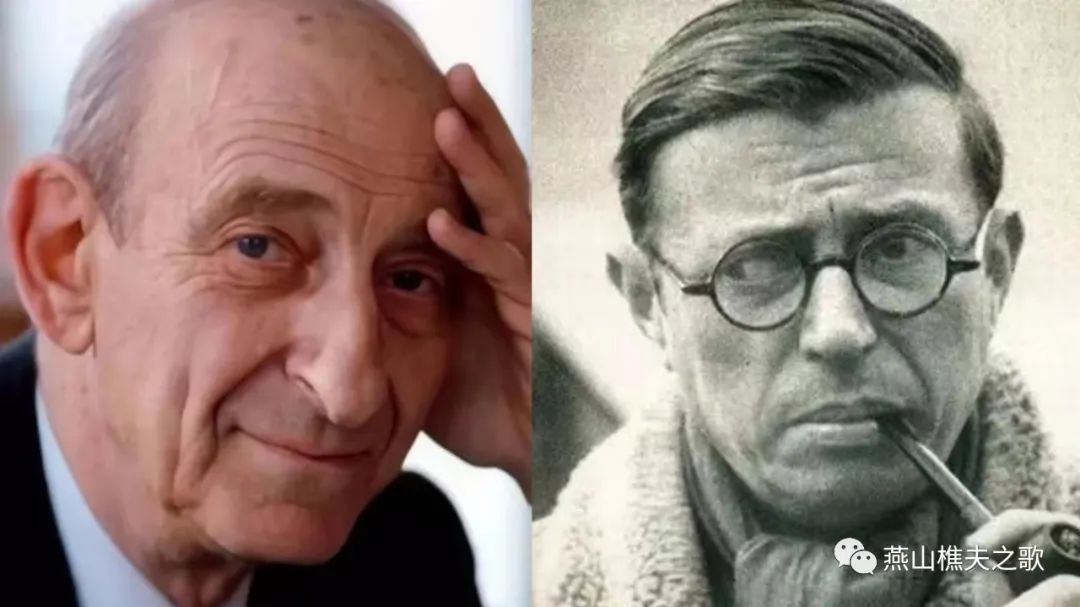
作者按:本文是“世纪批判三书”之第一卷《世纪的歧路——左翼共同体批判》中的一章,主要阐述法国战后的左右之争:雷蒙·阿隆与萨特长达三十年的思想战争。有人曾认为20世纪有三场大辩论意义重大,兰格与米塞斯、罗尔斯与诺奇克、萨特与阿隆,他们之间的思想分歧与冲突涵盖了社会经济制度、伦理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三大战场,对人类社会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果这个判断成立,那么,雷蒙·阿隆与萨特的世纪之争,不管从持续的时间来看,还是从影响的范围来看,无疑占据着20世纪思想斗争史的首位,其内容广泛地涉及到哲学、政治、历史、文明、制度、价值观、意识形态和世界秩序等各个方面,对当下的思想和理论建构有重大的启示。本文六万余字,分八个部分展开,分八期发表。
目录
引言
萨特的世纪及其挑战者
第一回合:冷战与意识形态的大决裂
第二回合:左翼的分裂与知识分子的鸦片
第三回合:三大事变与左右之争的激化
第四回合:阿尔及利亚悲剧与民族主义考验
第五回合:关于五月风暴的争论与反思
第六回合:“古拉格群岛” 与左派的危机
最后回合:历史没有终结
引 言
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法国思想界便一直处在剧烈的动荡与冲突之中。连绵不断的革命进程与其说是社会政治经济内在矛盾的爆发,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毋宁说是法国长期陷于思想分裂与意见纷争的结果。基于不同思想和学术背景的知识分子对法国政治生活的“介入”,深刻地影响了法国的社会与政治变迁。以“德雷福斯事件”为标志,1埃米尔·左拉发出的“我控诉”,就像是对法国知识分子在20世纪集体出场的召唤,也是预示着“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垄断着国家的思想、知识和意识形态生产的共同体迅速进入到左右之争的轨道。诚如美国学者托尼·朱特所观察到那样,20世纪的法国始终处在涣散飘摇之中,政治上的左右两派争个没完没了,维希政权及其对民族道德境况的恶劣影响延续了数十年之久,政治制度的持续不稳重现了19世纪的情形——法国第四共和国只存续了短短十四年,政府平均每半年更迭一次。他受雷蒙·阿隆的启示,把法国20世纪以来这些显而易见的症状统称为“法兰西病症”,认为它们直接来源于对法国共同历史,特别是法国大革命遗产的相互冲突的解释,来源于因为意识形态一分为二所导致的“左派”和“右派”的分野。由此形成了一个人们普遍共有的认识:
//
“左右之争及相关的政局不稳,是法国面临的最重要、最紧迫的难题,因为这些问题深深植根于各种政治记忆之争,植根于有关‘真实的’法兰西历史道路的各种叙述之争。”2
在法国左右两派的世纪之争中,让-保罗·萨特与雷蒙·阿隆无疑是这两个对立的思想阵营的旗手,前者高举着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甚至毛主义的旗帜,将罗伯斯庇尔、卡斯特罗、切·格瓦拉式的革命者奉为大众的榜样,终身都在为抗拒资本主义的邪恶而向往着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后者则高举着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旗帜,将孟德斯鸠、托克维尔、马克斯·韦伯视为自己的理论前驱,终身都在为抵抗极权主义制度而坚守着宪政民主的立场。在萨特和阿隆的身后,是穿越了20世纪法国的两条不同的政治和思想轨迹,以及被他们浓重的身影所笼罩的各种历史事件和人物。如何书写发生在这两位“小同学”之间的长达三十年的“思想战争”,是法国思想史叙事无法回避而必须回答的问题。法国著名作家安德烈·纪德是有先见之明,他在1943年就认为:“在法国,总是存在分裂和党派斗争(除非受到一种共同的压力),将来还会存在;这就是对话。多亏了这种对话,我们的文化才得以保持平衡:一种百花齐放的平衡。”3为证明这个观点,他把帕斯卡和蒙田、克洛岱尔和瓦莱里视为他们时代思想对立的两极。纪德“忘了”提醒人们的是,在他的时代,思想对立的两极是由雷蒙·阿隆和让-保罗·萨特构成的。

萨特的世纪及其挑战者
历史学教授米歇尔·维诺克在其撰写的《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一书中,用三个法国思想家的名字来象征20世纪的三个时代——巴雷斯时代、纪德时代和萨特时代。他认为:“莫里斯·巴雷斯是德雷福斯事件至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时期的象征;安德烈·纪德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一时期的象征;让-保罗·萨特是法国解放以后这一时期的象征。”4对于萨特时代之所以能够取代纪德时代的依据,维诺克是基于萨特在战后几年已经形成的巨大公共影响,这不仅体现在萨特统治着国家的主要舆论舞台,以致几乎所有人都认识他,还在于他从纪德那里接受的不是同一个时代和同一份名单。在二战造成的法国的思想和文化废墟上,萨特是携带着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文学成果以及《存在与虚无》这部存在主义哲学巨著,为法国重建精神世界带来了新的希望。因此,哲学家贝尔纳-亨利·列维更愿意把法国的20世纪称为“萨特的世纪”,他所看到的居于“绝对主宰地位”的萨特,不仅拥有当时绝无仅有的公共影响力,还在于——
//
“萨特是这一代人中的惟一。他以独一无二的能力,尝试了绝对的作品,在他之后,任何其他人都不曾作过这种尝试。”
比如,梅洛·庞蒂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但却不是一个作家、戏剧家,也不是一个艺术家,“尽管他想努力改变自己,可他仍然无可救药地只是一个教授”。加缪是记者、是作家、是戏剧家,甚至还是政治家,但他不是一个哲学家。至于雷蒙·阿隆,是一个哲学家,但他和梅洛·庞蒂一样,不是一个作家。正是基于这样的比较,列维为赋予20世纪以萨特的名义而得出结论:“总之,在这一代人,只有萨特擅长于所有文体。只有他一个人占领了所有可供占领的阵地。”“萨特是惟一使当时的文学和文化空间达到饱和的人。”5更有甚者的是,这位哲学家还把萨特与戴高乐相提并论,认为萨特是另一个戴高乐,而戴高乐则是创造历史的萨特,他们构成了20世纪一对真正的作家和政治家的联盟。

以萨特的名字来命名法国的20世纪,这并非是思想史家们的溢美之词。雷蒙·阿隆的回忆录曾记载了萨特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读书时所抱有的宏大理想:与黑格尔齐名并尽力超过黑格尔。6这是萨特为自己所做出的历史定位,此时,他和阿隆一样只有二十几岁,但改造法国思想世界的种子已经植入在他的志向之中。
//
西蒙娜·德·波伏娃——萨特的终身伴侣,他们互相忠实于对方的思想而不是身体,由此为法国开创了一种新的两性关系——对萨特的过人之处下过定义:同时成为斯宾诺莎和司汤达,也就是同时成为卓越的哲学家和文学家。7
萨特显然完成了这个世人无法完成的使命,按照列维的说法,这是在伏尔泰或雨果的时代都不曾有过的事情,而萨特的历史性出场,“斯宾诺莎—伏尔泰—萨特形成了一条轴线”,再加上具有与司汤达和雨果相媲美的文学成就,萨特无疑成了法国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第一个——也是惟一的一个——集理论家和天才文学家于一身的人”。8
从“萨特的时代”到“萨特的世纪”,这是一个价值判断,更是一个事实判断,至少有两个现象学事件可以用来证明萨特在战后法国的巨大公共影响力。一个事件是发生在1945年10月29日,萨特在巴黎举行了题为“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演讲,完全出乎所有媒体预料的是,演讲大厅被无数听众挤得水泄不通,许多妇女因为室内空气稀薄而出现晕厥,这是公众渴望了解萨特1943年出版的《存在与虚无》这部艰涩的哲学专著的创作意图,也是公众盛情迎接他“介入”法国政治生活的一个象征。就演讲稿本身而言,这不过是“一部应景之作”,是《存在与虚无》的通俗版,只是标志着萨特“知识分子生涯的第一次转变”。9 但就是从这个演讲开始,萨特的世纪可以用存在主义来命名了。或者说,一个存在主义时代到来了,其繁荣的标志不仅仅是萨特出版物的畅销,而且还涌现出存在主义的生活方式,诸如存在主义咖啡馆、以黑色为标记的存在主义服饰,成为巴黎流行的时尚。萨特的哲学被“当成是生活的实用手册或求生指南”,10抽象的形而上学被演化为浪漫主义的煽情风格或愤世嫉俗的生活姿态。
另一个现象学事件是,1957年,法国著名的新闻周刊《快报》,就1945年萨特创办《现代》杂志以来所形成的思想新浪潮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其中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您被要求在下列作家中指出对您这代人有特别影响的一位,您会选择谁?”结果是大多数年轻人把萨特放在首位,其得票数远远高于安德烈·纪德和弗朗索瓦·莫里亚克。11这个事件被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认为是萨特“荣耀”时代的到来,甚至可以被视为同伏尔泰和左拉一样,在生前就被认为是一个神话的开始,它不仅体现出人们对参与政治的知识分子的尊重,也体现出萨特在法国公众中的实际影响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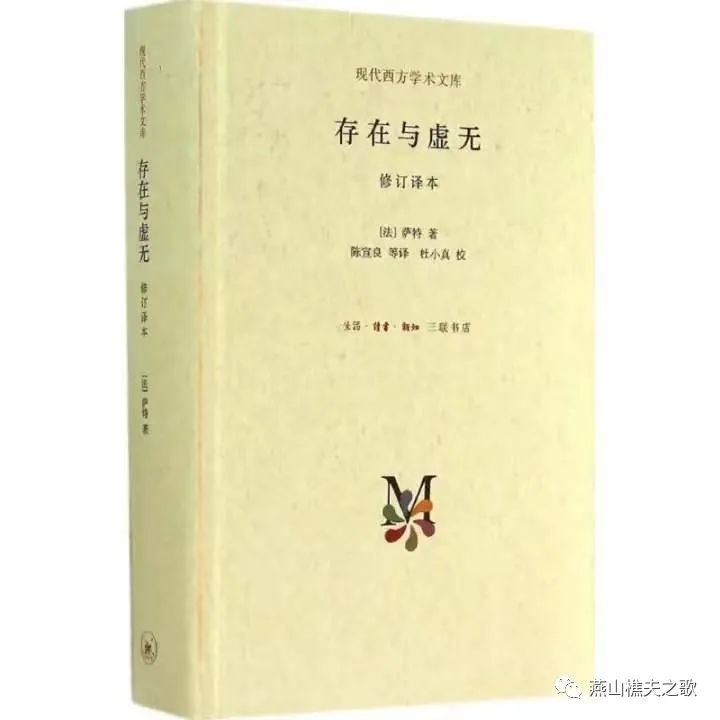
在确定谁能成为法国的“世纪之人”时,列维提出了他的一个看法:“谁能从精神上站在由当时最有吸引力的力量汇聚而成的焦点上,不管是依靠本能还是依靠算计,谁就是‘伟大的知识分子’。”12他认为萨特就是一个“伟大的知识分子”,但他似乎并不清楚萨特究竟依靠何种“秘术”让世界围绕着他的轴心而转动。这个问题对于其他观察家来说也是存在的。萨特在1944年以前还是一个不问政治的人,他的文学作品尽管已有极大的影响,但他的《存在与虚无》并没有多少人能读得懂。萨特在1945年突然“爆红”,究竟是在何种时代条件和社会机制下产生的?法国独特的政治结构和思想结构,究竟为萨特势不可挡的崛起提供了何种温床?
托尼·朱特观察到,法国二战之后的十年间,左翼阵营的苏维埃共产主义的诉求几乎处于垄断地位,其重要性体现为大多数法国政治思想家都受其影响,这一现象在西方国家独一无二。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了一个实例,在二战过去二十年之后,一位斯洛伐克犹太人约·朗格尔惊诧于她在巴黎的经历:“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对其经历的否认,对历史证据的视而不见,以及对放弃正统的革新论神话和乌托邦的拒绝。”她毫不客气地认为,这个被困在时间舱的群体“是早该消亡的物种”。13朱特是试图借助于来自东欧国家那些饱受共产主义迫害的异见分子的亲身体会,以揭示他们与法国左翼知识分子之间的一种巨大认识差距,解释为什么诸如萨特这样的文化英雄可以在“布达佩斯遍体鳞伤”之时,依然在国内广受追捧、声名显赫和备受尊重。这类“法国病”,正如雷蒙·阿隆在其《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完全得益于法国长期的左翼传统,即得益于从法国大革命以来所形成的三个“神话”:左派的神话、革命的神话和无产阶级的神话。三个神话导致的后果是:
//
“知识分子对民主国家的缺失毫不留情,却对那些以冠冕堂皇的理论的名义所犯的滔天大罪予以宽容”。14
在法国的政治辞典中,自“德雷福斯事件”形成“知识分子”这一概念以来,“‘知识分子’和‘左翼知识分子’是同义语”,15随后它又和共产主义紧密相联。斯大林格勒之战对于扭转二战局势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在许多法国知识分子的心目中转化为共产主义的胜利光环。更重要的是,法国共产党在1945年成为法国第一大党,这是共产主义在法国凯歌行进的具体体现,它自称是“法国知识分子”政党,其政治势力在知识界有广泛的建树和影响,诸如物理学家皮埃尔·居里和艺术家毕加索在战争结束后宣布加入法共,成为当时的标志性事件。战后完成政治觉醒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更是纷纷被吸纳到法共的各级组织中。萨特领导的《现代》杂志也不例外,其左翼的立场也是根据共产主义的坐标为自己定位:如果不是成为共产党人,也必须成为共产党的“同路人”。萨特是从共产主义运动中获取了灵感,同时,他的理论与行动为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来自左翼的最强有力的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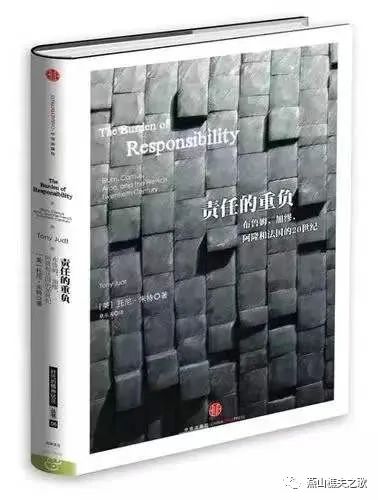
左翼和共产主义的联盟,在法国知识界形成了双重优势,进而形成了一股在年轻人中广泛盛行的进步主义潮流。朱特在他的著作中引述了社会学家雅尼娜·韦尔代-勒鲁的一个有代表性的看法:“老派的左翼知识分子可能会将选票投给共产党,甚至寄希望于一个马克思主义式的将来,但是他们无法全然忘记《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也无法忘却苏联在30年代令人伤脑筋的内部档案。然而,对于更年轻一些的人而言,他们不在乎过去发生了什么,并急于将其抛之脑后;他们所看到的是,党派发起的政治运动回应了他们自身对进步、变化和剧变的渴求。”16年轻人渴求改变现状的强烈冲动在萨特的理论中得到了回应,萨特把革命上升到绝对命令的高度,波伏娃对任何场合的改良主义的蔑视,以及对借由一场轰动性的、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发生方式的社会变革的希望,成为一种他们同时代人所共享的感情,也成为“萨特世纪”最坚实的和最广泛的心理基础。
在萨特形成的空前的话语攻势下,形形色色的各种右翼思想和理论都显得相形见绌,只剩下招架之力。雷蒙·阿隆对此深有体会:“在法国,左派享有的威望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温和的或保守的党派也绞尽脑汁从对手的词汇表中借取某些修饰语。人们彼此比试着谁最有共和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信念。”17在这种思想结构中,几乎没有人能够站出来挑战萨特的话语“霸权”。即使是萨特左翼阵营中的亲密战友,如加缪和梅洛·庞蒂,先后与萨特决裂,公开著文批判他的共产主义倾向,但在萨特的反击之下他们都不敢恋战,实际上承认了他们不是萨特的对手。加缪是在萨特的公开责难下加快了退出政治写作和公共生活的步伐,直至他1960年意外死亡才让萨特恢复了对他的友情与善意。
在所有萨特的反对者中,只有阿隆才是萨特的真正挑战者,他从1947年与萨特分道扬镳之后,几乎以一己之力承担起批判萨特的重任,因为在他看来:“无论是在巴黎还是在全世界,萨特都是以一个作家和一个伟人的形象活在我们心中。我认为我们有权利不受任何约束地评论他和描写他。”18阿隆终其一生都坚守着这个立场,不是屈服于而是挑战萨特至高无上的权威,以此捍卫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基本价值观。法国战后由左翼知识分子开创的“光辉的30年”,实际上是阿隆与萨特“思想战争”的30年,更确切地说,是阿隆持续批评萨特的30年。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阿隆看起来根本不是萨特的对手,他是处在思想界的边缘地带,不是时代的中心人物,也不是公众舆论的代言人。在代表着重建法国时代精神的哲学和文学领域里,阿隆还没有创作出足以和萨特相匹敌的作品,这是他从不讳言的事实,他坦承与萨特雄心勃勃的构建原创性和体系性思想比较起来,存在着差距。即使阿隆认为萨特哲学是一个失败,但他还是认为这是一个辉煌的失败。在无情地批评萨特的同时,阿隆从没有忘记真诚地赞美这个强大的对手。托尼·朱特说得对:“阿隆一直是萨特最好的、最富有同情心的读者和批评者。”19 1940年代末期,《快报》主编赛尔旺-施莱贝尔曾试图把他的一篇文章的题目定为《让-保罗·萨特与雷蒙·阿隆》,这遭到了《法兰西晚报》主编拉扎雷夫的反对,他认为:“这两个人不能相提并论”。20阿隆赞同这一看法,他从没有想过把自己的著作同萨特的著作进行比较,尽管他也承认从1968年以来,人们把他和萨特置于一起研究“已经不像过去那么离奇了”。21他自觉地意识到了与萨特长达三十年的争论并非是个人之争或门户之争,而是关系着法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和知识分子的前途,用他自己的话说:“身处的从来就不是一场善恶之战,而是一场更优更劣之战”。22对于萨特来说,他终其一生都对阿隆刻意保持着一种视而不见的态度,他从不认为这位“小同学”具有与自己旗鼓相当的公共影响力,也不愿意在电台和电视台上与阿隆进行公开对话,他甚至说过这样的话:宁愿与女人谈琐碎的小事,也不愿与阿隆谈哲学。但是,在众多观察家的眼里,萨特和阿隆作为法国战后左右两翼最有代表性的思想家,无可替代地占据着这一时期法国思想界的中心位置。西里奈利在研究萨特与阿隆的竞争性思想关系时就认为:“萨特和阿隆是双重意义的世纪文人:他们没有远离尘世,以酝酿和雕琢他们的作品,相反,两人都融入了他们那个时代的历史,尽管这一选择是在不同时间作出的;于是,他们通过表明立场和参加辩论,接受了汹涌热烈的20世纪。”23
事实上,这两位法国思想斗士的世纪之争所制造的巨大的历史惯性,早已穿越了时间和空间的屏障,在21世纪的时代条件下依然持续震荡,其意义对于理解中国当下的思想斗争依然具有重大启示。
本文注释:
1“德雷福斯事件”发生于1894年,法国陆军参谋部犹太籍的上尉军官德雷福斯被同僚诬陷犯有叛国罪,被军事法庭宣判革职并处终身流放。1896年,新任情报官皮尔卡在调查中发现,真正的罪犯不是德雷福斯而是他人,但军方蓄意包庇真正的罪犯,不对此案进行平反,由此引发社会公愤。左拉在《震旦》报上发表致总统的公开信——“我控诉”,推动了要求重审德雷福斯案件的社会运动,法国分裂为德雷福斯派和反德雷福斯派的两大阵营。1899年8月,案件重审,德雷福斯仍然被判有罪,但改判十年徒刑;9月19日,总统决定赦免德雷福斯,以平息民愤。1906年7月,最高法院撤销原判,德雷福斯被平反,恢复名誉,并晋升为少校。德雷福斯经此事件而成为“拿破仑死后最出名的人”,相关的参考书籍超过了一千两百种,此外还有电影、戏剧、诗以及一出三部曲歌剧。“德雷福斯事件”最具标志性意义在于让左拉名垂史册,使其成为法国知识分子介入社会事务的典范,同时开启了法国知识分子分裂与斗争的历史。参阅[美]迈克尔·伯恩斯:《法国与德雷福斯事件》,郑约宜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
2[美]托尼·朱特:《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章乐天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8-9页。
3转引自[法]米歇尔·维诺克:《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萨特时代》,孙桂荣、逸风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5页。
4[法]米歇尔·维诺克:《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巴雷斯时代》,孙桂荣、逸风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5-6页。
5参阅[法]贝尔纳-亨利·列维:《萨特的世纪》,闫素伟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70-74页。
6参阅[法]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上卷,杨祖功、王甦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42页。
7参阅[法]贝尔纳-亨利·列维:《萨特的世纪》,第95页。
8同上书,第95页。
9参阅[法]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第8页。
10[法]贝尔纳-亨利·列维:《萨特的世纪》,第27页。
11参阅[法]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20世纪的两位只是分子:萨特与阿隆》,陈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28页。
12[法]贝尔纳-亨利·列维:《萨特的世纪》,第119页。
13[美]托尼·朱特:《未竟的往昔:法国知识分子,1944—1956》,李岚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4页。
14[法]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吕一民、顾杭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1页。
15[法]米歇尔·维诺克:《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巴雷斯时代》,第2页。
16[法]雅尼娜·韦尔代-勒鲁:《为党派服务》,转引自托尼·朱特:《未竟的往昔:法国知识分子,1944—1956》,第51页。
17[法]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第4页。
18[法]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下卷,第693页。
19[美]托尼·朱特:《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第252页。
20[法]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下卷,第694页。
21同上书,第694页。
22转引自托尼·朱特:《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第267页。
23[法]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20世纪的两位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第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