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行法国(13)这一天我成为了法国女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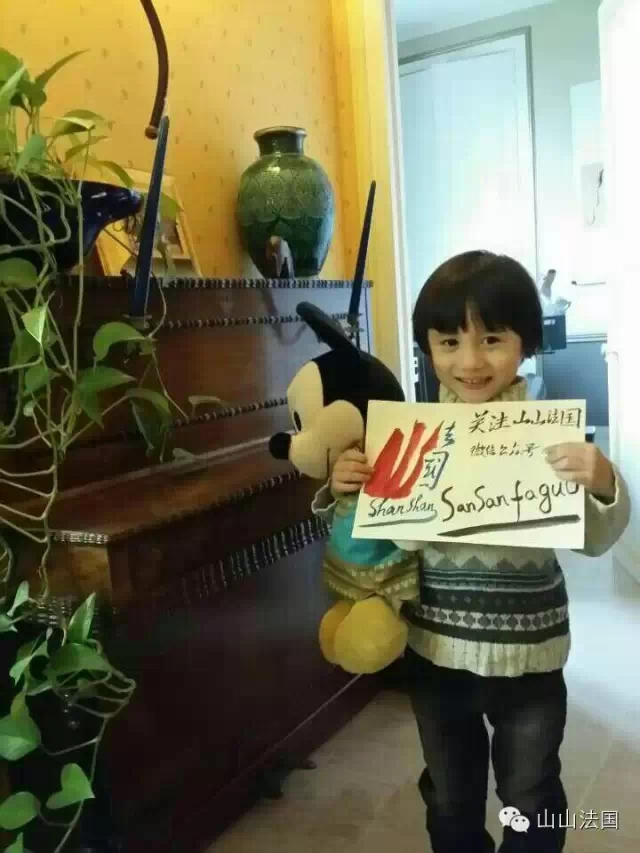
孙山山四子(二任德裔法籍妻子生)
荷马.孙(Romain.Su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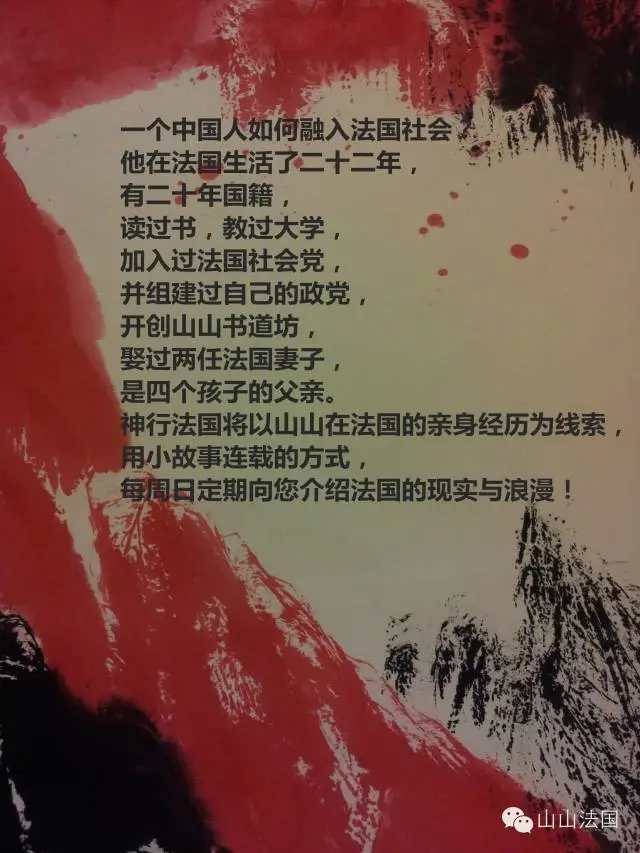
神行法国连载(十三)
这一天我成为了法国女婿
文:孙山山(法国)
1995年夏天

我们坐在行往波列塔尼的高铁上,小雪照样拿出书读着,她专注的样子总使我想起法国画家仁奥诺·佛哈戈纳(Jean-Honoré Fragonard)的《阅读的女孩》。那年她23岁,她有两个妹妹,小妹只有10岁,还有个弟弟。
这会儿我想和她说话,就不停地打量她,小雪猜到了我的心思,暂时把书放下来。你怕见我父母呀,她冲我一笑。我才不怕,我见过他们的照片,还通过电话。小雪的眼睛最美,她没有浅色的眸子,她的目光那么澄澈而深邃,笑起来的时候,露出两个酒窝,就是这张纯洁的面孔使我爱上了她。
受小雪父母的邀请我来到了法国, 1994年12月我们在巴黎办了结婚手续。这次回布列塔尼,是为了感谢小雪的父母同时举行我们的婚礼。


我一落脚布列塔尼,才觉得我的法国生活应该从这里开始,我在巴黎混了一年多,与其说我和法国人在一起,毋宁说我和世界公民在一起,巴黎不仅仅属于法国,为生活奔波的面孔,无论是哪一种肤色都必须烙上地铁,活儿和睡觉(Métro,boulot,dodo)的印迹,人们在这里盲目地追随着世界之都的节奏。
这个靠近英吉利海峡的小城叫科昂(Créhen),房屋清一色由黑色板岩盖顶,石头的房基,房子的周围开满了绣球花(Hortensia)。天那么蓝,草坪那么绿,房子那么独立……仿佛在童话里一样。



我们到的时候,她的妈妈、弟弟和两个妹妹站在花园的门口迎接我们,那是除了小雪之外,我第一次拥抱我的法国亲人。我很激动,但有些局促不安,我东张西望为了掩饰内心的波动。这时我看见在花园的尽头,有一个男人正在浇花,我想他就是小雪的爸爸。如果是今天,我绝对不会想为什么她的爸爸不来迎接我们,我甚至会说,我想你就是小雪的爸爸,叫约瑟夫……






但当时我就顺着这个情绪一直爬上去,越爬越高,我的脚离地越来越远。我紧紧地靠着小雪,与她寸步不离,我们上了楼,把行李放在她的卧室,这会儿我噗通一下落在地上,暂时轻松下来。我没有词形容她的卧室,除了白色还是白色,她的床和电影中白雪公主的一样,我那么爱这间卧室!直到小雪说,你不是想看海吗?我们现在就去!仿佛我并没有听见,喉咙有什么塞着,我想我的确被带到了天堂。
这是不是太多?还能接受什么?我无法伸出我的左手,也无法伸出我的右手,如果点头也是手,转身又是另一只手,还有微笑……我愿意站着不动。这时楼下有说话的声音,那会儿还不是是吃饭的时间,她妈妈却叫她的大妹玛丽娅姆去地里摘西红柿……
卧室的窗户紧闭着,我想把窗户打开,我把手插进裤袋,想掏出一支烟,看着那两片洁白的窗帘,又把手缩了回来。小雪已经下楼去了,我还是把窗户打开了,远远望得见邻家的草坪,但看不见一个人。这么安静,太阳并未打算敛起它的光芒,更远的深处你能辨认出大海的蓝。美使我开始害怕,我甚至想到再钻进巴黎肮脏的地铁,再从肮脏的地铁钻出来,那里有一个中国朋友在等我去喝啤酒。



和小雪的家人一起吃饭,依然是刀叉,依然是头盘和正菜,我那么拘谨。我每次把头抬起来都得想好看谁。她的弟弟吉尔达长得很像他姐姐,看他就等于看一个男的小雪,就好像已经认识他。可是她的大妹和她的小妹妹芮芮,正好坐在我的对面,她们蓝色的眼睛直逼着我。
事实上她们根本就没有在吃饭,她们在看我;她们根本就没有看我,她们在等我出丑。我尽量不把刀叉弄响,吞咽的时候,也像他们一样,一点声音也没有。中国有笑不露齿的说法,法国人却有吃不显齿的讲究。规矩的人家吃饭讲究安静,除了朋友聚会,吃喝时有说有笑,但我的老丈人老丈母还不是我的朋友。
那会儿我很想喝酒,可是主人不给你倒酒,就没得喝,这也是规矩。她的妈妈罗莎琳也看我,那是出于主妇的习惯,还问我好吃吗?塞崩!塞崩!(C’est bon!C’est bon !好吃!好吃!)那会儿我的浪漫情绪略有抬头,但很快就“塞崩”了。
小雪就在我的身边,她也知道我喜欢喝酒,为什么不给我倒上一口,我塞得快崩溃了,她都不救我。约瑟夫也在观察我,他使我想起在西双版纳认识的美国朋友考利·龙瑞克,吃饭的时候我总担心食物会挂在他的唇须上,但是饭都吃完了,也没有挂上去。约瑟夫留着稠密的唇须,我怯生生低头看见的只是他蠕动的胡子。他自个儿掺酒喝着,我的那半杯红酒早就见了底,他可能在等我说出,我也喜欢喝葡萄酒。我试了几次,都说不出口。




不曾有人引导我,也没有神引导我认识小雪,可是我感觉到我必须做我该做的事情,我一个人在布列塔尼,一个人在巴黎,就像我一个人在中国,我为什么不这样看世界,而是那样看世界?我以为我是个奇怪的人,一个离群索居的人,间或一个疯子。可是我还是能够碰到那个和我亲近的人,那就是小雪。
她把我带到了法国,从巴黎到布列塔尼。现在在一个小村庄,一个连星星的鼻子眼睛都看得清楚的小村庄,一个到了夜晚,夜莺和夜莺约会的声音都听得见的小村庄。我们躺在床上,小雪正准备拿起书来,我一下撑起身来,我说,我们真的有一个婚礼?

我一点儿准备都没有,我当然准备好了,我的意思是谁会主持我们的婚礼?因为我什么都没有,我有的就是我。
我从旅行包里搜出那块一丈见方的扎染布,小雪一下扑倒在我的身上,她当然知道我的绝活,用绳子把白布或者纱扎起来,扔进染缸,再把绳子解开,那种你等也等不来的花纹,突如其来的美丽让你兴奋。记得是画家张金贵教给我的这个手艺,在中国小雪已经和我一起做过扎染。
我要给你缝制一件婚纱,这会儿,她用她的双手使劲地摇动我的双臂,她从被窝里钻出来,站在地上,我从穿衣镜看见她卷起的睡衣,她的大腿和脚,我一下想把她抱起来,我想吻她,并和她做爱。
她再一次扑向我,我知道她为什么一下变得如此无拘无束,因为她知道我喜欢把不会做的事做好……我没有缝制过一件衣服,为了小雪,如果我想,我一定能够做到。我的悲剧就是我的想象力,当有人喜欢我的想象,就是悲剧的开始,而这个悲剧就是我在中国无法实现的梦想。



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亲戚们陆陆续续来到小雪父母的家。那么多人,其中包括刚果总统的亲兄弟伊萨姆。一切早已安排就绪,我却蒙在骨子里。约瑟夫身着笔挺的西装,和平时判若两人。这会儿他对我微笑,眼神诡谲而调皮,那意思是,看你的了中国小伙子!
直到覆盖着玫瑰的婚车开到花园的门口,我一下子明白了什么。别人要把女儿嫁给你,就像把他们自己的生命交出来一样,我的泪水悄悄流了下来,我要冲过去拥抱小雪的爸爸和妈妈……
小雪手倚着门框,在她父母的陪伴下,出现在大家的视野。掌声和欢呼声使她的头微微低下,等她再抬起头来,眼泪已挂满脸颊,她笑得好快乐,蓝色的扎染婚纱穿在小雪的身上特别耀眼,不是耀眼是独一无二!
这时大家把目光投向我,也许他们觉得这套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的婚纱是绝妙的选择。我用了7个夜晚缝制这套婚纱,我的手上不知扎了多少个洞。我的脸上也不知印上了多少小雪的吻,她紧跟着我走到我想象的尽头。一定要这样去做,因为我不想她穿上和别人一样的婚纱。
我穿着一身崭新的中山服,脚蹬千层底手工布鞋,这也吸引了大家的目光。我牵着小雪的手蹬上了婚车,芮芮把绣球花环扣在我的头顶,玛丽娅姆给我献上了一束玫瑰花。

一共有20多辆车浩浩荡荡的来到迪南(Dinan)的一家米其林三星级餐馆。席间大家要求我唱一首中国歌,我就唱了《东方红》。我在中国不知唱了多少次《东方红》,但这一次我唱得最好。
专栏编辑:周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