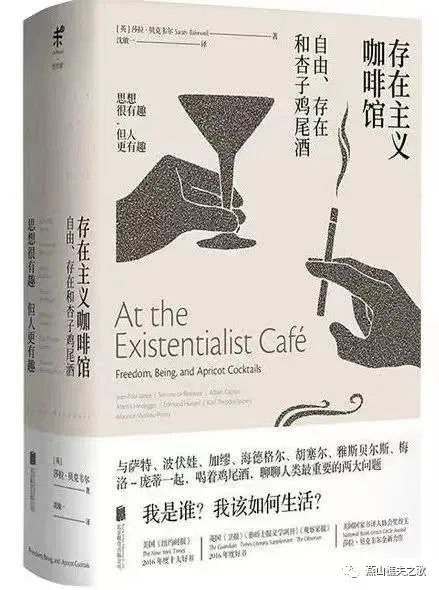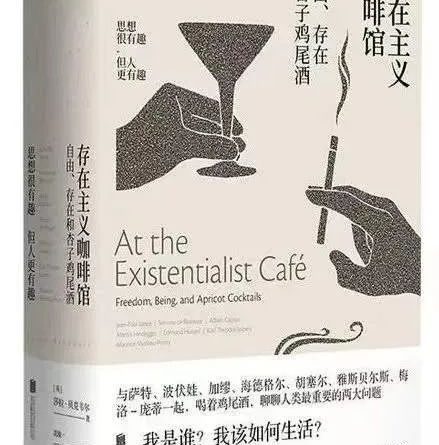雷蒙·阿隆与萨特的世纪之争(八)
——最后回合:历史没有终结
鲁越
1979年6月20日,这个看似普通的日子,却被许多思想史学者记录在他们的著作中。因为就是在一天,让-保罗·萨特和雷蒙·阿隆在他们决裂之后的三十年里第二次握手。1阿隆在他的回忆录中认真地记载了这个时刻:为声援“开向越南的船”这个人道主义组织实施救援越南难民的行动,萨特和阿隆共同参加了该组织的记者招待会,阿隆在与萨特握手的刹那脱口而出:“你好,我的小同学”——这是他们最初的身份定位,永远没有改变。他们握手的照片后来被一百多个国家买去转载,成为新闻报刊热议的一个主题。著名作家克洛德·莫里亚克把“小同学”错听成“老同学”,他为此谈了自己的感受:“这个词使我感到吃惊。在他们分道扬镳如此之久后,这个称呼显得流于俗套,不够味,别扭,然而仍然令人感动”。2阿隆则不这么看,他在致莫里亚克的信中专门对“小同学”这个称呼做了解释:“这是要抹去30年的分歧,重新回到50年前的一种姿态,因为在高师,我们这个小圈子里都互相称呼为‘小同学’”。3阿隆非常看重这次握手,因为当他看到萨特双目失明、近乎瘫痪时,心中充满同情和无限怜悯,他能感觉到这位“小同学”正向死亡走去。
波伏娃在《告别的仪式》这本萨特晚年编年史中也记述了萨特与阿隆“长时间来第一次握了手”的时刻,但她认为记者们宣称这是一个政治上的和解、意味着萨特在立场上开始接近右翼的看法,是大错特错的,因为“萨特并不认为他和阿隆的会见有多重要”。4这是他们对阿隆一如既往的态度:在道德上始终藐视他的存在,在政治上和他永不妥协。波伏娃甚至把阿隆在致莫里亚克的信中所表达的对萨特的同情与怜悯解读成“我好像看到了一个死人”,5这种偏执的心结在三十年后仍然没有化解,真是一个悲剧。对于许多观察者来说,他们倒是并不在乎萨特和阿隆在握手的瞬间究竟会说些什么,他们看重的是这个事件的象征性意义:
“萨特—阿隆的积极行动象征着法国政治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意识形态的诉求已经丧失了优先性。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建构法国政治的左右分裂似乎已经丧失了它的至高权威。反而一种新的人道主义情感占据了主导地位”。6

理查德·沃林的这个看法可以被这个时期的许多事实所证实,萨特晚年也的确表现出一些前所未有的思想变化。1974年8-9月,萨特在与波伏娃的对话中明确认为,苏联不再是社会主义,法共也不再是革命的,并且认为法共没有希望“焕发青春”或“发生改变”,年轻一代不会为党提供新鲜血液,反而只能使其更加僵化。7萨特对于“第三世界”革命的信心也在衰退之中,继对毛的文革幻想破灭之后,他与卡斯特罗政权也断绝了关系,因为该政权不顾他和其他众多著名人物的情愿,执意将古巴著名异议诗人赫贝托·帕迪拉判处死刑。诗人的死刑后来尽管没有执行,但萨特和卡斯特罗长达十几年的友谊宣告死亡。萨特能够和阿隆一起参加“越南难民之船”行动,表明他从1960年代以来一直支持印度支那解放事业的立场上转向了人道主义立场,意识到越南难民逃离的正是北越红色政权所施加给南越人民的大规模人道灾难。1980年1月,离萨特去世只有三个月时间,他在欧洲广播电台上发表声明支持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安德烈·萨哈罗夫,同时呼吁抵制当年计划在莫斯科召开的夏季奥运会。
阿隆注意到了萨特从1968年以来所发生的思想变化,即从一个把革命和共产主义以及苏联等同起来的共产党“同路人”,转向毛主义所倡导的个人或集体实践的自发性,最后“重新找到了自己的真正归宿——无政府主义”。同时,萨特也开始小心翼翼地与暴力哲学切割,“不再允许为了崇高的目的而犯罪”,转而“同情受专制政权,甚至是受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专制政权迫害的人”。8阿隆认为,正是由于这一点,他们才可能在反布尔什维主义的钟声中走到一起。但是——

阿隆很清楚,和萨特握一下手绝不可能消除持续了30年的隔阂,他关心的是“我们之间的握手对于历史学家是否有什么象征性的意义”?是不是该到了总结他们世纪之争的时候了?尤其是在萨特去世之后,思想史研究者包括社会公众不可避免地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归根结底,萨特和阿隆两人之间究竟谁更能标志出那个时代的历史呢?”9
在托尼·朱特看来,阿隆的自由主义是在被延误了差不多30年之后才在其“自耕地”上繁荣兴盛,他在大部分成人岁月中一直是个孤独的背影,直到生命之火燃尽前夕才翻身。西里奈利也有差不多相同的看法,认为对萨特和阿隆的对比性研究“只有被放到70年代临近黄昏的历史背景下,才会体会出它的全部意义”。10历史是最公正的裁判,真理是在时间之流中逐渐显现出来的。在萨特和阿隆的世纪之争中,可以确定的事实是,前者的大部分预言一如前述都遭到了历史的否定,而后者对现实和历史趋势超乎常人的远见则不断地被证实。左翼知识分子基于革命、暴力和恐怖的政治梦想全都流产了,而自由知识分子则在阿隆的率领下实现了重要的思想突破,在法国深厚的左翼文化氛围中坚守并扩张了自由主义的理论阵地。
法国左右两翼长期失衡的力量对比关系,通过阿隆持续不断的拨乱反正,终于达到了某种思想平衡,法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对革命和暴力近乎病态的崇拜,日趋被温和的、理性的和改良的进步主义思潮所取代,并且在反对苏维埃“古拉格”统治模式上形成了新的共识。

列维在《萨特的世纪》中提出过这样的问题:“萨特的后半生完全是在犯错误呢?这是不是说,他在斯大林时期和后来的毛时期,没有干好事,只不过是让他的名字和他的权威蒙受了世纪的耻辱,成了二十世纪最大的盲目行为的受害者?”11列维自己认为“显然不是的”,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在同一时期可以列举许多情形来说明萨特还是伟大的、宽厚的、清醒的,他是小人物和社会底层的朋友,热爱正义、权利、自由和友谊,时刻准备为受压迫者的事业而燃烧自己。在列维的视野中,实际上存在着两个萨特,一个是“好”的,无可指摘;另一个是“坏”的,迷失了方向,十足可悲,不断地犯错误,并引导着时代和他一块儿犯错误。两个萨特也可以称之为“早期的萨特”和“后期的萨特”,前者以《厌恶》和《存在与虚无》为代表作,塑造的是典型的文学家和思想家的形象;后者则是以《共产主义者与和平》、《全世界受苦的人》的序言和《辩证理性批判》为代表作,塑造的是典型的革命者和共产党的同路人的形象。两个萨特并非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不断地互相腐蚀,互相传染,互相控制,早期的萨特预示着后期的萨特的狂热和对暴力的喜好以及对主体的蔑视。12列维关于两个萨特的看法表明,探讨萨特思想两重性的深刻根源,是思想史研究者无论如何都无法回避的事情。阿隆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曾提到过两个萨特的概念,即在一个激进的萨特的背后有时还是能够看到一个年轻时代的萨特形象,尤其是在萨特进入生命的最后时光里,阿隆注意到这位“小同学”正在试图重新接受一个“复数”的思想,那就是在与别人的思想交流中分享有别于自己的思想。萨特说了:“这是一种只有当我衰老时才可能想到的交流方式”。13但是,阿隆并不期待萨特在其晚年会有根本性的思想觉悟以及与别人平等讨论的勇气,他认为:
“萨特的灾难在于他总有一天要受到世人的谴责,因为他把自己能言善辩的口才和丰富的情感都用来为不合理的事物辩护,他滥用自己的宝贵才智,试图向人们证明斯大林是不能反对的。”14

萨特确如阿隆所概括的那样,在任何时期都拒绝做任何自我批评,从不理睬别人对他的言论的奚落讪笑,他在晚年只承认过一个错误,那就是“不够激进,而不是因为过分激进”。1975年,萨特在与米歇尔·贡塔的长篇访谈中断然否决阿隆对他的所有质疑,尤其是认为阿隆对《辩证理性批判》的批判“歪曲我的思想以便能更好地提出异议”。15 1980年3月,法国《新观察家》周刊分三期连载了萨特和贝尼·莱维(“五月风暴”时期的学生领袖维克多的真名)的长篇访谈,这是萨特生前最后一次谈话,却被波伏娃认定是一个“屈打成招”的谈话,因为莱维“巧舌如簧,把萨特说得晕头转向,不容他静下心来下结论”。16她最不满意的是莱维以披露事实的名义扮演了萨特代理人的角色,而这个角色原来一直是属于她的,由她在掌控萨特的话语权。当访谈录以《今天的希望:与萨特的谈话》为题公开发表之后,波伏娃从萨特的反应中实际上知道了他对自己生命中最后这份文字记录是抱有很高的期待。萨特在访谈中首先表达的是一种悲观主义的情绪,那是在莱维的“诱导”下确认人类的行动朝向未来的目标时最后都是毫无结果——始终存在着一种失败。但萨特强调他从不绝望,从不认为失败是不可抗拒地必然趋向那具有绝对因素的目的地,他在这个最后的谈话中仍然没有放弃为法国左翼知识分子指明航向的使命,强调左派必须继续坚持激进主义的传统:“不论是什么情况,对我来说,激进主义似乎始终是左派的一个基本观念。如果我们拒绝激进主义,我们就在不小的程度上促成左派的死亡。”17不仅如此,萨特在回答莱维提出的“暴力是否证明是正当的”以及“暴力是否有助于制定法律和制度”的问题时,再次为暴力提供辩护,强调为了推翻被殖民和被奴役状态,除了用暴力解决之外,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同时——
萨特继续为革命提供道德证明,承认“作为革命的最终目的的道德观念可以设想为一种救世主义”,革命派要创造一个更令人满意和更合乎人性的社会,其实就是一个公正的社会和道德的社会。18他最后的期待是:“再一次把希望视为我对未来的概念”。19

阿隆在读到萨特这份对话录时,不能不感到遗憾:“表达这种真相的文章又是何等的贫乏,何等平淡无奇而又令人感到费解。”20他把萨特承诺给未来的希望视为“在人类历史上对救世主的期望”,因为萨特终生都在尝试扮演一个救世主的角色,他所设计和想象的各种终极性的革命救赎方案,尽管看起来充满令人心动的愿景,最后都是随着他向往的共产主义革命模式的崩溃而成为政治幻灭的标志。对于阿隆来说,他绝不会去做一个萨特式的人类命运的预言家,而宁愿选择做一个冷静的理性的现实观察者,在对现实的批判中为国家和社会的进步提供建设性方案,这是他走出巴黎高师之后一以贯之的身份定位。1981年10月,阿隆决定为自己做一个三集的电视节目,节目是对自己理论生涯的总结,主线索是他和萨特“两个小同学之间历时30年的对话”,最后是要向观众解释:“我为什么会选择走一条与那些和我同时代的名人所走的截然不同的道路”?21谈话节目的文字版被整理成一部著作——《介入的旁观者》,确定这个题目,显然也表明了阿隆对自己身份的清醒自觉。当“介入”这个词汇成为左翼知识分子的专有名词时,一如托尼·朱特所说:“阿隆则用完全的严肃态度对待介入的本原含义,并且为它添加了一种执着和一以贯之的独特精神。”22阿隆是以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以及不屈从于任何意识形态的压力而为自己开辟道路,他最珍视的价值观是“真理”与“自由”,在他看来,这两个概念是密不可分的,对真理的热爱和对谎言的憎恶深刻地体现在他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里,他拨开意识形态的迷雾所揭橥的诸种历史真相,终于为他赢得了历史的名声——20世纪法国最清醒的政治评论家、最伟大的思想导师和最坚定的自由主义战士。
阿隆在生命行将结束时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包括来自左翼阵营的思想对手和萨特拥趸的认可。萨特《七十岁自画像》的合作者米歇尔·贡塔在读完《介入的旁观者》之后,承认在30年的敌对之后,“长期把阿隆视为人所不齿的对手,把他拒之门外的左翼知识界,如今发现自己成了或几乎成了阿隆派”。他认为阿隆和萨特的对话代表着本世纪对立的两极,知识界的辩论在这两极中展开:“一个陈述所希望的、令人想望的东西,提出一个不确定的计划;另一个理智地用可能做到的事,用顽固的现实与之对抗,要人们警惕”。23但他最后还是为萨特进行了辩护,强调了被压迫者基于伸张正义的唯一权利而起来反抗时,他们的这一权利不能被否定。对于来自左翼的赞誉或误解,阿隆并不太在意,他在意的是萨特和自己背道而驰的终极性根源:如何选择自己认为的最有利于人类的社会或政权——这是最初的最原始的选择。
阿隆始终认为,萨特的根本问题在于,他否认现实,却对自己要创造的未来一无所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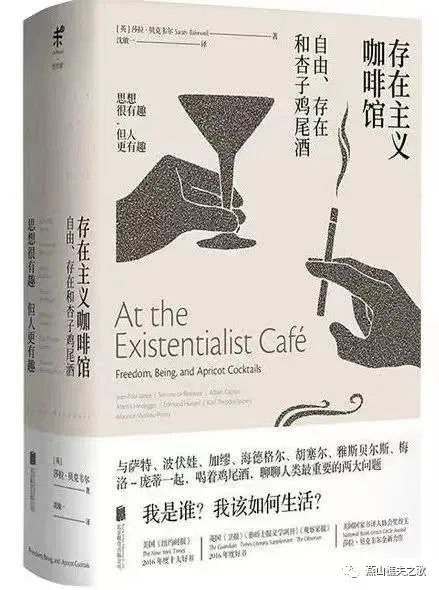
1983年春天,阿隆的回忆录出版,这是一部费时四年完成的史诗性巨著,副标题是“50年的政治思考”,旨在突出作者与20世纪密切联系的精神历程。该书出版成为轰动知识界的大事,售出了数十万册,法国新闻界几乎一致交口称赞。阿隆在回忆录中所开放出来的磅礴思潮,迅速打开了人们记忆的闸门,让他们汇入到法国历史的主流中进行重新思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米歇尔·维克多,也就是最后与萨特对话的贝尼·莱维,致信阿隆表达他的敬意,他检讨了他这一代人在法国知识界的心理环境中曾长期远离阿隆的大部分著述,甚至将阿隆视为资产阶级的“看门狗”,但是,他最终认识到阿隆著作的价值所在:“随着知识分子的非马克思主义化,我们开始真正发现了你。回顾往事,我佩服你迎着风浪,顶住来自你的天然环境,来自知识界的压力,坚持自己的立场。单凭你早已有的把政治分析与感情分开的愿望是不够的,你还需要平静超凡的精神勇气。如今的报复多么痛快淋漓。”24法共专家雅尼娜·韦尔代-勒鲁在读了回忆录后也给阿隆写了长信,深刻反省以前受了蒙蔽而根本“听”不进他的著述,怕丢掉无法估价的左派标签而不能正视他的意见,现在她认识到:“读你书的时候,我想起尼采讲到作为强者被接受的人时讲过的一句话:‘不需要极端信仰的人最稳定。’而你的书是一部强者的书”。25这些迟来的赞誉和认可,是法国知识界还阿隆一个公道也是还一笔债,在阿隆被他们集体流放了30年之后,他们终于认识到了这位自始至终都对苏维埃式意识形态及其制度绝不妥协的人,才是法国知识界真正的良心,他对思想世界和公共生活英雄般的贡献,谱写了法国知识分子“光辉的30年”中最灿烂的篇章。
1980年4月15日,让-保罗·萨特辞世长眠,按照波伏娃的说法,他平静地迎接死亡,对周围的友谊和感情心怀感激,对自己的过去感到满意:“该做的,我都做了”。26这是客观得不能再客观的自我评价?在萨特的灵车前往蒙巴纳斯公墓的路上,一股巨大的人流跟在后面,大约有五万人,有人说这是1968年运动以来的最后一次游行。在送葬的人群中,最伤心的是波伏娃,她和萨特是精神共同体,是他众多女友中唯一终身不离不弃的伴侣,死神却让他们永远分开。雷蒙·阿隆对萨特的去世同样怀有巨大的悲痛,他们在50年前有过约定:谁后走一步,就要为先去世的人在高等师范学校的同学录上撰写一篇生平传略。阿隆深感遗憾的是,诺言已经不复存在,长达30年的“思想战争”无可挽回地摧毁了他们之间的情感基础。即使阿隆没有,萨特也肯定有,埋藏在心底的一些仇恨至死无法化解。所以,阿隆把公正评价萨特的权利交给了别人,从追思的悲悯情怀中走向了自己的终极思考,这是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之所以加速撰写回忆录的动力所在:在面临上帝召唤的时刻,完成自己最后的使命。

1983年10月7日,雷蒙·阿隆因心脏病发作猝然而死,他在死神来临之前亲眼见证了自己的回忆录成为出版界的盛事——“我相信,我已经说出了基本事实”,这使得他在告别人世时毫无遗憾。巴维雷兹评述了萨特和阿隆不同的死亡方式:“萨特漫长的暮年不公正地给他整个一生涂上了暗色,阿隆则幸运地在心智健全时,带着因姗姗来迟而更加辉煌的成功的光环离开舞台。”27虽然阿隆的葬礼远没有像萨特那样轰动,但他的离世依然震惊了世界,亨利·基辛格表示“没有雷蒙·阿隆,世界将感到更加孤独,而且更空虚”;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向“主张对话、信念坚定、学养深厚”的阿隆致敬。法国最著名的报刊纷纷发表纪念文章:《解放报》悼念文章的标题是“法国失去了自己的教师”;《世界报》为“清醒和睿智的教授”拿出了三个纪念版面;《新观察家》特别是《快报》发表了“一位超凡出众的知识分子”的大量报道。28在肃穆的安静的气氛中,阿隆被葬在和萨特同一个公墓——蒙巴纳斯公墓,这是象征他们最后的归宿,比邻同眠,永续他们生前不竭的恩怨。
让-保罗·萨特和雷蒙·阿隆都走了,持续了30年的“思想战争”终于终结了,但历史并未终结,他们开创的20世纪的思想、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之争,在21世纪的时代条件下还在继续进行着,苏东体制的彻底崩溃完全符合阿隆的预期,但未必是萨特终身倡导的革命的激进的左翼的意识形态的烟消云散,“历史,再度面临重大的转折”(汤因比语)。令人欣慰的是,“作为一位法国爱国者和世界公民,作为一位共和派与自由主义者,作为一位政治思想中心人物和自由战士,阿隆对行走于21世纪历史之陡峭道路上的人而言是最好的旅伴”。29人们将持续不断地从他的著作中汲取智慧、力量和勇气,在他的鼓舞下对人类社会自由和民主的未来充满信心。

本文注释:
1 1960年某天,萨特和阿隆因为他们共同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而在一次街上的偶遇中握手、互致问候并约下饭局,这是他们自1948年以来的第一次握手,但饭局没有后来始终落实。参阅雷蒙·阿隆《介入的旁观者:雷蒙·阿隆访谈录》,第167页。
2 参阅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下卷,第1052-1053页。
4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告别的仪式》,第135页。
6 [法]理查德·沃林:《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第259页。
7 参阅西蒙娜·德·波伏娃:《告别的仪式》,第486-489页。
8 [法]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下卷,第1056-1057页。
10[法]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20世纪的两位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第366页。
11[法]贝尔纳-亨利·列维:《萨特的世纪》,第555页。
13转引自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下卷,第1064页。
14同上书,第1069-1070页。阿隆对这段话做了一个说明:在这里我应该说不能反对共产主义。
15[法]让-保罗·萨特:《七十岁自画像》,《萨特文学论文集》(《萨特文集》文学卷),第391页。
16[法]西蒙娜·德·波伏娃:《告别的仪式》,第139页。
17[法]让-保罗·萨特:《今天的希望:与萨特的谈话》,《萨特哲学论文集》(《萨特文集》哲学卷),第192页。
21[法]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下卷,第1073页。
22[美]托尼·朱特:《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第267页。
23[法]尼古拉·巴维雷兹:《历史的见证:雷蒙·阿隆传》,第434-435页。
26[法]西蒙娜·德·波伏娃:《告别的仪式》,第145页。
27[法]尼古拉·巴维雷兹:《历史的见证:雷蒙·阿隆传》,第439页。
29[法]尼古拉·巴维雷兹:《序言:雷蒙·阿隆和普世史的时代》,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上卷,第28页。